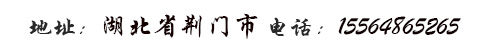小时候,家乡的春天特别纯粹
|
泉州白癜风医院 https://m-mip.39.net/nk/mipso_5779684.html 日前豆瓣阅读举办了线上“方舟沙龙”,邀请了我社新书《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的作者沈书枝,和大家一起聊了聊“逝去的乡村和童年”:一个充满着闪光细节的乡村,一个充满着私人回忆的童年。为大家献上活动实录。 沈书枝 大家好,我是沈书枝,很高兴今天在豆瓣阅读的方舟沙龙跟大家聊一聊逝去的乡村和童年。首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安徽南陵人,是一个80后,之前出过散文集《八九十枝花》,最近刚刚出版了我的第二本书《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 其实之前我很有些犹豫到底要跟大家聊什么,有想过聊一聊乡村的四季,但实际上关于乡村生活,我最喜欢的、最记得的、在我性格里可能也是刻下印记最深的事情,其实我的两本书里已经差不多都写过了。读过我的书的读者,可能对这些都已经熟悉,而有些像我一样从乡下长大的朋友,可能又会觉得这些自己小时候都经历过,不需要我再来说。 所以我有点惆怅,不知道跟大家说这些有没有意义。豆瓣阅读的活动海报上写的是“一个充满闪光细节的乡村,一个充满私人回忆的童年”,那么我还是就从这里入手吧。想先跟大家聊一聊乡村生活的“常”与“变”。“常”就是平常的“常”,“变”就是变化的“变”。既有从从前延续到现在都相同的“常”的一面,也有早已经完全不同的“变”的一面,在“变”的过程里有“常”,而“常”的日子往往也已经被各种变化所方方面面渗透。 我生长的地方在皖南一个小乡村,风景和建筑不如大家一般所熟悉的宏村、西递那么好看,是一个典型的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村。像现在,时间到了三月,我在北京,整天刮着大风,天气还很冷。零零星星地开了的花,只有迎春花、杨树花这样普通或者不起眼的花。到处是灰扑扑的建筑——当然其实不只北京如此,我们很多城市都这样。地面上不是水泥的地方就是光秃秃的黄土,或者枯黄的草坪。这是我在北京工作的第五年,每到春天的时候,我的思乡的情绪就特别汹涌,特别怀念家乡的春天,尤其是小时候的春天——因为它特别地纯粹,非常完整自足,跟自然非常接近。 在家乡,差不多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到田畈去,到山上去”。我们村子上十几户人家,聚集在一起。房屋旁边就是大大小小小的水塘,大概有六七个,水塘绵延分布在几十里路的稻田之间。在我小时候,每家在秋冬天晚稻收回去之后不久,就会在田里撒上油菜和紫云英(我们称为“红花草”或“草籽”)的种子,到春天紫云英碧绿的叶子就已经长得有一尺来高,开满密密麻麻的蝴蝶一样的紫红的花。油菜也差不多在同时开花,绵延几十里路的田畈,除了村子和水塘,放眼望去就全是紫云英红的花和油菜黄的花。那样的场景,即使是看惯了的、也不太懂得什么是“美”的小孩子的眼里,也是非常美丽而且令人高兴的。 给大家看两张紫云英的图片。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想找到一张像我小时候看到的那种绵延几十里的紫云英花的照片,但是很难找到跟我记忆中比较相像的。反而是动画片《辉夜姬物语》里的这个场景,比较接近于我小时候看到的田野的样子。 紫云英的花(图片来自网络) 《辉夜姬物语》 这张也有点接近乡下紫云英开时的样子,虽然这只是一块田(图片来自网络) 乡下人种紫云英是为了肥田,等到春耕的时候,就把它犁到田泥下面,渥烂了做田里的绿肥。但在春耕之前,我们也会到田野掐紫云英还没开花的嫩茎,回去清炒来吃,很好吃的。更多的时候,是割回去在大锅里加米和水煮成粥喂猪吃。 这个时候,田里还会有另外一种开小黄花的稻槎菜,因为它喜欢田里去年收割过后留下的枯的稻槎旁边,所以叫这个名字。它贴在地上长着,田里田埂上到处都是,那时候我们叫它“黄花菜”。我们春天放学以后,放学的路上看见长得好的稻槎菜,就要用小刀把它挑起来揣在书包里带回去。到家以后,也几乎每个傍晚都要拎着篮子,拿着铲子,和村子上其他小孩,或者家里的兄弟姐妹一起到田里挑猪菜。要挑满大半篮子,才回去给妈妈,让她切碎了拌在潲水里喂猪。 我们小时候做着这些事,很开心的,因为家里很穷,你即使是小孩子,也要懂得为家里出一点力气,那么挑猪菜这样简单的等同于玩的事情,我们都很高兴去做的。挑猪菜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边去紫云英田里掐花来玩,把花串成一串,做成项链挂在头上、颈子上,在一大片紫红的花田里找一朵纯白的紫云英花,假如找到了,就很高兴。遇到长在紫云英花田里的稻槎菜,它因为阳光被紫云英遮住了,长得非常细长柔嫩,挑出来油绿绿的,我们觉得好看,有时候也会把它拿到头上,像花一样戴一戴。所以小孩子其实是很有自娱自乐的天赋的,你不用怎么教他,他也会在劳作中找到一些游戏的愉悦。 去年清明节,家门前 这张照片是去年清明节,我回家的时候,站在我家二楼上拍的。这是站在二楼可以看到的我家门前的样子。因为下了好多天的雨,到处都是水,看上去都像水塘一样。其实里面狭长绵延的那一带是水塘,剩下方块的都是水田。因为一直下雨,远处的村子和山都看不见了。 到清明前后,田里的农事就忙起来。要把去年留下的或者去农业合作社买来的稻种泡到塘里,等稻芽出来了,再撒到精耕细作的秧田里。两边插上竹片,绷成拱形,上面蒙上塑料薄膜,等秧苗长出来,天气暖和了,再把塑料薄膜揭掉。秧苗长到十几厘米,就要做大田,准备插秧。 做大田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做田要做四遍,灌水、犁田、耙田、耖田、朗田,每一遍工具和程序都不一样,媒体上大家见到的常常只是犁田一节,所以实际上,以前做田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每一道工序都靠人和一头牛来出劳力做,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偷懒。田耕不细的话,稻子长不好收成不好,收入就减少了。 田做好了,就要插秧,春天插秧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我们那里,每年第一天插秧的时候,为了事情能做得快一点,常常要请村子上的人或者亲戚一起去插新秧,回头自己有空就去还工。这一天这家的主妇要专门煮茶叶蛋、包粽子,送到田埂上给插秧的人吃。 这是我小时候的事,现在我们那里种田也和以前不一样,要稍微轻松一些了。大家不再专门做秧田,而是直接把大田做好,把发芽的稻种撒到做好的田里,让它直接在田里发芽,省去了插秧这一道手续,要省许多力气。 可能有人要问以前为什么不这样做吗?因为现在有收割机了,到了夏天收割机开来,十几亩田一天就割掉了,以前没有收割机,要一棵一棵地用镰刀把稻割倒,摞成一摞一摞的,再用打稻机打,假如不一行一列地栽得非常整齐的话,就没法收割。现在有收割机就没有这种限制,所以现在可以直接在大田里播稻种了。收稻也不再需要多少人力,也轻松多了。 这是我去年回家拍的,上面那张是端午前后,单晚稻稻种刚刚在田里发出来的样子,还稀稀疏疏的,看起来听不好看的。不过水稻的发棵能力是很强的,不就之后就长成下面这张照片一样密密麻麻的。像这种稻的话,用镰刀是完全没办法收割的,只能用收割机来割。 大人在田里忙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做什么呢?清明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事情是上山掐蕨菜刚长出来的嫩苗,我们称为“蕨蕨禾子”。也是提一个篮子,村子上的小孩子约好了一起去远处的山上,在矮矮的山坡上这里找一下,那里找一下,新生的蕨蕨禾子拳头还没有展开来,像小猫小狗的小爪子。 去年清明上坟路上所掐的蕨蕨禾子 这张照片是去年清明节的时候,我和家人上坟回来的路上,看见了蕨蕨禾子就顺便掐了一些回来。蕨蕨禾子长了很多毛,很可爱。回来之后,用开水烫一下,切段加腊肉一起炒来吃,是很好吃的。我们掐蕨蕨禾子因此也很开心,又玩了,又觉得自己给家里挣了一碗菜,很不了起。和暮春的时候到山上拔野生的水竹笋子是一样的道理。 掐蕨蕨禾子的时候,山上的映山红花差不多也同时开了。我们那里的山上都是红土,长得很多的映山红,我小时候春天花开的时候,有的山上真的漫山遍野都是。我每想起家乡的春天,就会想起青绿的山野里忽然一树的映山红。我感觉映山红接近于我乡愁的代表。前一阵子,我在给大家签《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签名本的时候,很多上面都写了跟映山红有关的话。我实在太喜欢这种植物了。虽然我家里离山有一定的距离,我小时候上山的机会其实很少,也就春天这一两次,秋天去打茅栗子一两次。 去年清明节上坟时拍的映山红 我们把映山红的花掐来吃,折一根枝子,把花掐来,把尾部和花蕊去掉,一朵一朵串在枝子上,串成一个长串来吃,酸酸甜甜的。不过这里多说一句,大家不要随便在山上吃杜鹃科的花,因为好多都是有毒的。对映山红不是特别熟的话,在山上不要随便采着吃。我们那里的人对映山红都有一点特殊的感情,我们小时候上山去掐蕨蕨禾子,下山的时候,多少还会掐一抱映山红花带回去,养在房间里,是我们那里的人为数不多的珍惜好花的时候。 有一个爷爷掐了一抱,要带到城里去给他孙女 我们也掐了几枝回来,养在酒瓶子里 这两张照片也都是我去年清明节回去的时候拍的,我们上坟回来,经过一户人家,去他家挖笋。在他家堂屋里,我看见他摩托车后面绑了一束掐下来的映山红,我问他干嘛,他说要到住在泾县的儿子家去,他孙女叫他掐一束映山红带过去。所以他特意去山上掐了一把,过会准备走了,就把映山红绑在车上。我当时看到很感动,所以就拍了一张照片。 那天我们也掐了一点,不过我长大了性格也变了,也不怎么舍得掐花。对于映山红,因为我有特殊的感情,还是挑了一两枝开得不怎么好的,摘回来了,放在我爸爸的酒瓶里面,放在房间里,就像小时候一样。那个时候,我们不管是去山上掐了映山红花,还是去村子东头掐金银花,都是这样养在酒瓶里。有一点过去的风味,所以觉得很亲切。 《辉夜姬物语》 所以我看《辉夜姬物语》时,尤其是前半段,感觉那就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再现。我很喜欢里面那首歌,小孩子唱着“鸟儿、虫子和野兽,青草树木和花,带着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快快到来”,一边指着路边的“青草!树木!花!”。是在劳动和玩耍的过程中接受了自然与人生的教育,觉得特别亲切。我小的时候,没人给我美的教育,还不觉得乡下怎么好看,但长大了离开家乡,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就小时候曾经觉得平淡无奇,甚至是平庸乏味的家乡生活,其实也是很美丽的。 这是我去年不同时间回去时所拍的家乡的照片,离我家很近,也就不到一里路的距离。这些场景我从小就看惯了,一点也没觉得他们美丽。但是现在的话,很久不回去,心里就会觉得思念和不舍。我现在离开乡村太久,并且成人之后,风景在眼中可能有点变得审美化。所以刚刚和大家说一点小时候的事,可能还有一点我担心的牧歌化在其中。但乡下生活确实有其朴素动人的一面。 同时,在乡下成长的经历使得有些事情永远也不会改变。比如我永远也不会把一片油菜花田或紫云英田视为纯粹的自然的美景。每当我看到春天盛开的油菜花田,所涌起的感情,总是掺杂着油菜可以收割榨油的农业作用的亲切感。每当我走在荒地里,看见长得非常好的草,第一反应也总是想起我小时候放的那头牛,想着要是它还在,遇到这么好的草该多好。看到田里的稻槎菜,心里就觉得欢喜,因为可以喂猪;看见风吹落的很好的干树枝,心里也很可惜,想到这么好的树枝,却不能像小时候那样捡回去当柴烧。这大概是十几年的乡村生活在我身上留下的最令我珍惜的痕迹,它使得我成为我自己。我的朋友舒行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一段话,大概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觉得很好,读给大家听一听: 加里·斯奈徳说的:“我们的地方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地方,在我,就是这些山、村子、这高处的草地……是一切童年时踏过的地方,我的语言、举手投足,都有这个地方的痕迹。 下面讲讲关于“变”的部分。《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的第一篇长散文《姐姐》,是写我三个姐姐读书、恋爱和从农村到城市扎根的故事,第二篇长散文,是写我和我的双胞胎妹妹的《双子》,从小学到高中的故事。实际上,我们姐妹五个从出生到成长,以及从农村最终走入城市,正好是赶上社会急剧变化的那个年代,我们成长的经历,因此也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同时大约也反应了我们那一代人在时代里的遭遇。 我们出生于农耕社会还非常稳定、足以自我完善和循环的时代,在童年时期完整地经历过田野生活的辛苦和快乐,到上初中的时候,打工潮涌入乡村,绝大多数同龄人念完初中以后就没再上学,以前,是回家种田、嫁人,那时候就变成跟着大人一起出去打工,吃许多苦,挣一些钱。 当然,打工吃苦还是比种田要好,因为那时候种田更辛苦,挣得更少。另外很少一部分人,则接着念高中,念大学,像我和妹妹那样,靠念书“出来了”。我们的经历和遭遇,可以说都是很普通然而又是很典型的。 农村也在这时候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因为绝大多数年轻人都离开,留在村子里的都是老人或者儿童。现在我们村子上儿童也很少了。还在种田的,除了那种承包了很多出去打工的人家不种的田的“种田大户”,就是我爸爸、我舅舅这一辈的人了。 我舅舅在村子里算是一个例外,他是唯一一个壮年的时候没有出去打过工的人,一辈子都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到如今六十岁了,还仍然是地方上种田的主力。所以我有时候焦虑,等到他们都种不动田的时候,谁来种田呢?只有种田大户吗?像我们这样零散的种田家庭将不复存在吗? 农村的确是在式微,这是暂时看上去好像无法扭转的趋势。年轻人绝大部分都离开农村了,没有离开的,也在县城工作,很少还有留在村子里种田的。还有的时候是拆迁,使得很多自然村消失,农民被迫进入了城里。 我在《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的后记里也说了,现在乡下也只有大路还有人再走,更多的小路,从前我们上学的路,现在完全消失了。人离开了,种田的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整田埂,于是荒草疯长,从前很宽的田埂现在都走不大通了。 我没有社会学的知识基础,也很难对比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见解,但总还对我从小长大、现在也时不时回去的农村抱了一种美好的期望,就是希望再过些年,我们的农村能够像日本的农村那样,也可以有便利的生活条件,比如装修得便于生活的房子,干净的水资源,更机械化的农业技术,那个时候,也许也会有年轻的一代重新回去吧。 给大家看这两张照片,也是我去年回去时拍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田埂都长满了水竹笋,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种田的人,他们夏天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扛着锄头,把自己家的田前前后后绕一遍。有没有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是不是漏水了;田埂上有没有长草啊,如果长草了,就把草铲掉。在以前田埂上长水竹笋,还长这么高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后面那张照片是我们从前上小学的路,我在书里也写了。那条路已经完全没有了,因为小学校也已经没有了。 我在看日剧《小森林》的时候,心里非常羡慕,因为他们的农村虽然也好像无可挽回地凋敝下去了,但生活在那里的人,生活条件是很方便、很现代化的,刨除电视剧美化的成分,至少过的也是一种无论如何都算非常方便的生活。 《小森林》剧照 这张照片是日剧《小森林》的一张剧照,是女主角的厨房。就像电视剧里面这样的厨房,在我们乡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便利的生活条件对家庭的影响有多大。很多村子到现在都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方便的公共交通,我们现在到镇上去,假如没有车,就只能走四十分钟。我们家一直到前年,我爸爸重新回家种田,才砌了一个可以好好洗澡的淋浴间,装了一个电热水器。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改善措施,我姐姐她们去年回家的次数就多多了,因为再带着小孩回去,洗澡就方便多了。这两年过年的时候,网上好像流行了一阵子把城市里的自己家和农村里的老家做对比,相比之下,有的老家实在是太破败、太不适合居住了,有的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好像农村这样落后,住在那里实在是非人的,过年快结束吧,快回到城市开始光亮的生活吧。我看见这样的话,心里总有些生气,因为你忍不住会想,难道连一床新的被子都不能买回去吗?那个地方就是这样确凿无疑要被抛弃的吗? 总之,我就希望农民也应该有权利不离开农村,却也能过上更好生活的权利和机会吧。 最后做一个小小的广告!欢迎大家去读我的新书《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这本书是关于我家姐妹五个从小到大,从农村到城市的故事,写得会更详细、更深入一些。 《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是豆瓣人气作者沈书枝历时三年倾情撰写的长篇散文力作,是一本完全关于童年与家乡的人事之书。 即使在乡下,像沈书枝家这样姊妹五个的,也实在很少见。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姐妹间相互的照顾与情感的羁绊,是作者童年及少年时期最宝贵的礼物。沈书枝以一贯细密工整的文字、冲淡平和的语调讲述着姐妹五人之间的情感和各自的人生故事,温柔地注视记忆中的自己与他人,朴素诚实地展现出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看似琐碎的讲述中,能让人静下心来感受平淡日子的冷暖,体味生活的质感。 ▌相关阅读点击下方标题即可阅读 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丨人文夜读 长按上图,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yinhuaa.com/jyhfb/5276.html
- 上一篇文章: 春天去赏花临沂最全赏花图鉴,美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