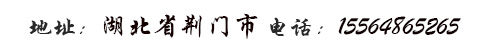ldquo夯尚rdquo半坡寨的
|
北京哪有治疗白癜风医院的地址 https://myyk.familydoctor.com.cn/2831/newslist_7_1.html 作者:石绍辉 一一年到头琐事缠身,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总想拥有一段清闲的时光。日思夜盼,终于到了辞旧迎新的日子,绷紧的神经总算可以放松了。没想到,放下手中的活儿,心里反倒像没根的秋蓬空落落的,思乡的情愫涌上心头,不招自来,挥之不去。从花垣去凤凰,沿着下沱公路一路前行,走过补抽乡政府所在地,再爬一道斜坡就到了一个名叫“夯尚”的村子。村子的四面是山,其中西面一座最大,从山脚仰望,山头似乎直插云霄,顶到苍穹。村口有一条被树木和杂草掩蔽得严严实实的进山小径。沿着小径往上爬去,只见山中有大小不一的坪地,坪上有高低不同的小山,山上又有形状各异的小丘。一层坪地一层山,一座山来数道丘。层层叠叠,连绵起伏,一头连着湖南,一头连着贵州。道光年间,这座大山水草丰茂盛,是个天然牧场。一天,夯尚村一个龙姓人家像往常一样把牛儿赶到半山腰放牧。夜幕降临,主人想要把吃饱喝足的牲口赶回山下,可无论怎么鞭打,它们都不愿离开。经不住鞭打的领头牛流着眼泪跪在了地上。牛通人性,人解牛情。“既然牛儿不愿离开,那就在这儿安个家吧。”于是,当家的把最勤劳的儿子龙老二“分封”到山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龙老二把一块块土地开垦出来,有泉水的坪地用来炼成水田,缺水的荒土就翻成了旱田,一垅连着一垅,一丘连着一丘,从山脚连到山顶;又用青石板铺成出工小路,一级挨着一级,从山脚铺到了山顶,铺到了田间地头。春去秋来,龙老二在这荒山野岭开拓出一份大家业;世代延续,一家人繁衍成了一个寨子。这个寨子名叫“半坡寨”。我在这个寨子出生,在这个寨子成长。寨子的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旮旯都有我深刻的记忆。二寨前有一段斜斜的、百余米的缓坡泥巴路,被人们踏成了宽三十公分左右,平整得像一个长长的木质马槽。远离寨子的“马槽”口,有块一丈有余的石板。这是寨里外出和赶场的必经之路。平日里,一到赶场天,寨里的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来到“马槽”口等待大人们赶场回来,我们把它叫“等场”。大人们还没有回来,我们不想干等,就在那大石板上玩起了抓石子、捏泥巴等游戏。等待中,日头偏西了,赶场的大人陆陆续续地回寨,有的带回了一袋油香粑粑,有的扛回一根青甘蔗,还有的称回一包水果糖……无论手头多么拮据,都没有人空手而回。所以,我们恨不得大人们天天去赶场,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等场”。冬天来时,寨子其他地方比往日略显寂静,但这段斜坡路反倒热闹起来。北风吹来时,我们知道冰雪将至。于是,持着柴刀到自家的竹林里,砍回一根手臂粗的山竹,截成若干小段,劈成两块,削平竹节,然后烤在火苗上,再把它撬弯,一对对的“滑板”就这样制成了。万事俱备,只待冰雪来到。冰雪从来没有失约,总会伴着一夜寒风悄悄到来。第二天早上,寨里山上,门前屋后,大坪小院,都盖上了厚厚的积雪,整个半坡寨变成冰雪世界。我无心欣赏这些雪景,推开家门,拿上两块“滑板”,一溜烟似的跑向寨前的“马槽”路。此时,小伙伴、青年男女们已经嗨起来了,各显神通,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独立的,也有接成“火车”的,从高处滑向低处。在“马槽”路中间留下两条长长的犹如火车轨道般的痕迹。我很快加入到滑雪的队伍中来,我最得意的独门绝技就是单脚滑了。当然,技术再好也难免会摔跟头,甚至摔得鼻青脸肿,衣裤全湿,但整个过程没有哭声,只有笑语。“我要摔着了……”几个大哥哥滑到表姐们身边时,歪着身子装作要倒下的样子,话音刚落,双手已搭到表姐们的肩上了。“你个狼咬的,快滚到一边去。”表姐们知道他们是故意的,羞羞地骂了一两句,用力地把他们推到一边。天黑了,小伙伴们被父母呼喊着回家。但让我疑惑的是,我们都相继回去了,大哥哥们和表姐们咋还不回去呢?三欢娱让我觉得冬天过得很快,冰雪世界真让人不舍。生活在半坡寨,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空虚。春天一到,我们就把娱乐场从寨前转移到后山。一场春雨过后,枯落一冬的山泉涨起来了,汩汩地流到水田里,灌满了一垅又一垅;一声声巨雷作响,睡了一冬的青蛙苏醒了,悄悄地从洞穴里钻出来,呱呱呱地叫个不停。白天,我们有的带着竹篓,有的拿着麻袋,呼朋引伴来到梯田里捡田螺。不一会儿,就满载而归。我们把捡回的田螺放进大水缸里,待它吐尽污泥,再打碎壳儿,取出田螺肉切成片剁成丁。炒到黄澄澄时,再拌一勺擂好的干辣椒,香气四溢,飘满全寨。晚上,我们把两节电池的手电筒加长成四节电池的,装上三点八的电珠,再拿个竹夹,全副武装地相邀到水田里捉鳝。梯田里,电光忽闪忽闪的,蛙鸣伴着人语,像赶场似的,好不热闹。我从来没有空手而归,要是遇到闷热的天气,收获就更加丰厚了。半坡寨的田螺捡不完,半坡寨的黄鳝也捉不尽,我们常常把吃不完的拿到场上去卖,刚到场头就被贩子们抢购一空。有的贩子没有买到,还付给我们订金,希望下场卖给他。田里的和田坎上全是宝。捉黄鳝的事尚未结束,田坎上的荼靡从根部和枝丫处长出新苔,肥肥胖胖的有手指般大小,掰下来,剥掉皮,吃到嘴里甜到肚里。金银花也开了,庄稼人从水里走到岸上去采摘,竹席、竹匾、竹簸箕全装满了,晒在坪场上和院子里,微风徐来,阵阵清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金银花最值钱,采上一个花期,足以补贴一季家用。四待到一春花事了,便是青草最茂时。先人们把两处最高的山留作牧场。每到夏天,小草长齐了,山上的斜坡和坪地成了绿色的海洋。寨里没有让这些青草浪费,家家户户都养牛羊,多则二十来只(头),少则两三头。双休日或暑假里,放牛的任务多半交给娃儿,或者尚未成家的青年男女。自从记事起,家里放牛的差事就落在我的身上了。把牛羊赶到山上后,我们把人员分成三五拨守在连接庄稼的路口,便“信马由缰”,不管不顾了。牛羊尽情地撒欢,我们就开始下棋、打扑克牌,或自导自演“回放”前一夜的电视剧。太阳落山时,牛羊已吃得腰圆肚胀,我们却还没有尽兴,又玩一局。不觉间,太阳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月亮已高高地挂在半空中,借着皎洁的月光,我骑着一头温驯的老牛回到家里。放牛的日子里,我们最怕和寨上二十来岁的哥哥、姐姐在一起。刚把牛羊赶到山上,哥哥就迫不及待地爬到一处较高的丘顶,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然后把两手捂成喇叭的样子,长长打了几个“呜呼——”,不一会儿,远处也回了几个“呜呼”。无法辨别“呜呼”来自哪个方向,但可以断定那是女人的声音。听到回应声,哥哥们就编造理由叫我们帮他们看守牛儿。交接完毕,人就消失了踪影。哥哥们走后,远处又会传来男子的“呜呼”声,我们这边的姐姐也一定会回的。蓦然间,身边又会冒出几个陌生的哥哥。临近我们时,他们会哼上苗歌,姐姐们立即回了过去了。你来我往,唱着唱着,那几个陌生的哥哥就已坐到姐姐们的身边了。我们听得起劲,姐姐们却不顾人情地支使我们离开去望牛守羊。我们也曾念过啰唆,可他(她)们会说:“莫讲啰唆。你们长大就可以支使我们的伢儿了!”五绿了一夏的青草变得枯黄了,牛羊不到处的黄茅草黄得发红,黄得发亮。秋收过后,大人们要赶在霜降之前,把黄茅草割回寨里当作过冬的柴火。不要小看那些干草,用他们煮饭炒菜特别好用,就连那些毫不起眼的草灰也是最好的肥料。所以,我们的后山黄茅草引来了两省四乡的人们来割。有黄茅草牵线搭桥,大家很快熟悉起来了。收完了庄稼,割好了干草,常支使我们看牛羊的几个哥哥相继给我们带回了嫂子;和姐姐们对唱的几个陌生哥哥变成了“姐夫”,到我们后山割草的大人变成了半坡寨的亲家了。忙了一年的大人们还不能清闲,又得为哥哥姐姐们张罗婚姻大事。那时,半坡寨的婚宴特别热闹。一场婚宴要进行三天三夜,不需要山珍海味,不需要美馔佳肴,只要四盘黄豆、四盘米粉、一锅猪肉、一桶包谷烧酒就够了。婚宴里,对歌是少不了的。参加宴会的单身男女青年倘若彼此有意,前辈们一眼便可以看出来,会想方设法安排他们对歌。哥哥和嫂嫂们就会端来一盘巴掌大的肥肉和一碗干辣椒侍候。不敢唱的要惩罚,唱不赢的也要惩罚。哥哥见弟弟要吃大亏,就站在背后悄悄地教他唱。婚宴里,古老话是必须的,而且是重头戏。婆家和娘家各请了一个“话师”。从古讲到今,讲丰收,讲富贵,彼此祝福。倘若新郎是姓龙,新娘是姓麻,还得讲讲这两姓的来历和渊源。古老话可以从夜间讲到第二天的午间。“从今以后,龙麻两家求富得富,求贵得贵,像鱼虾一样发得满海满洋,像树木一样长得漫山遍野,今年我们喝包谷烧,来年我们喝糯米酒。”最后一句是用比喻的方式祝福主家富贵双全,儿孙满堂。博得了满屋喝彩。六那么多的古老话中,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一段关于半坡寨的故事。原来,经过四代耕耘和省吃俭用,半坡寨第四代人把家业做大了。在那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却有一家人年产粮食达到石,于是,半坡寨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肥。半坡寨的富裕招了别人的眼红,官家要给半坡寨摊派交粮任务,流氓地痞常来敲诈。民国时期,两省边区匪患猖獗。小小的一个山寨一个月内竟然被土匪抢劫了11次。被逼无奈的半坡人在寨中建起了一个石堡,石堡下挖了一个巨大的暗道,又在石堡的门楼上装上一门土炮。土匪进村时,一声锣响,各家就把牲口赶到暗道,乡亲就躲在石堡里。一天上午,大多数人刚刚上山务工。一伙土匪想要乘虚而入。尚未出工的两个成年男人,一个指挥大家把牲口赶到暗道,一个指挥妇女小孩跑进石堡。待土匪赶到石堡时,寨里锣鼓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到访”的土匪以为寨里人多,不敢轻举妄动。没有僵持多久,守在土炮前的男人通过猫眼看出土匪胆怯,突然放了一炮。土匪吓得四散而逃,出工的男人听到炮声赶紧回寨驰援。在回家的路上捉到一个受伤的土匪。这一仗,半坡寨名声大振,鲜有人再敢来侵犯。我祖父被土匪逼得无路可走,从邻村转投到半坡寨,并在半坡寨成了家。后来,解放军来了,半坡寨的匪患彻底根除了,乡亲安心过日子了。半坡寨懂得感恩,把三个最优秀、最壮实的男青年送到抗美援朝的战场;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捐了半年的口粮,最后全寨人禁食48天,寨里很多人都饿死了。除了妇女儿童外,全寨只剩下四个成年男子。祖父临死前把最后的一点口粮让给了我的父亲。祖父死时,我父亲只有八岁。可怜的父亲在祖父死后,睡在寨中一块大石头上奄奄一息地哭着。活着的人听到哭声也跟着哭。一个老奶奶听到哭声,给父亲送来一块蕨菜粑,又带他去挖蕨菜和葛根。父亲活下了,后来在寨里人的帮助下,成了家。后来,便有我们……只有听了半坡寨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只要提起半坡寨的往事,我的内心就不会再空虚,人生有了方向,生命也有了意义。来源:团结报责编:石健图片:李艾家石琳等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尽快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邮箱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yinhuaa.com/jyhfb/5099.html
- 上一篇文章: 世界卫生组织女性有炎症不妨多吃4种菜,不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